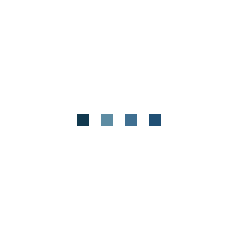吳芳銘/政治經濟觀察員
如果凱文・華許(Kevin Warsh)正式接任聯準會(Fed)主席,美國迎來的並不只是人事更替,而是一場貨幣治理哲學的轉向。
鮑爾(Jerome Powell)時代的聯準會,是一種「共識型央行」:高度制度化、重視前瞻指引、用模糊語言管理市場預期,在政治與金融之間維持微妙平衡。其核心精神是降低波動、平滑週期及避免突襲。
華許代表的卻是另一種路線——更接近「對沖基金式的央行」:快速判斷、風險優先,以及政策立場可隨環境劇烈而進行調整。
這不是單純鷹派或鴿派之別,而是「央行是穩定器」與「央行是主動風險管理者」的根本分歧。同時,這場轉變,也標誌著學術派退場、實戰派掌權。
從模型治理到市場治理
華許長期批評聯準會宛如「經濟學公會」,特別是對菲利浦曲線(Phillips Curve,通膨率與失業率呈現反向變動的關係,彼此有替代效果)與滯後數據的依賴。他認為,當以失業率與通膨數據進行趨勢確認時,政策工具往往早已錯過最佳時機。
亦即,華許明確反對鮑爾時代鉅細靡遺的前瞻指引框架,他認為對經濟數據的短期預測準確度有限,且經濟數據本身也是滯後的,故指引的準確度有限,反而會形成對市場的干預,華許稱之為「滾動式的咒語」來推動市場走勢(Moving markets with rolling Fed in cantations),並批評這框架讓聯準會成為市場波動的俘虜。
在他的世界觀裡,市場才是真正的領先指標。殖利率曲線、信用利差、資產價格、美元走勢及房地產流動性,這些即時訊號比滯後的官方統計數據,更誠實也更即時。數據只是後視鏡,市場才是前擋風玻璃。
這種思維直接承襲自其導師斯坦·德魯肯米勒(Stan Druckenmiller):經濟是可以交易的,政策是可以套利的,央行應像宏觀交易室一樣即時反應風險。
若華許主政,聯準會的決策重心將明顯從模型推演轉向市場感知。
高波動央行:政策不再溫和
鮑爾時代的核心原則是避免政策震盪;華許的邏輯則是「迅速修正錯誤」。
這意味三個可能變化:
第一,利率調整更劇烈。一次兩碼、甚至非例會升、降息可能不再是禁忌。政策路徑不再追求平滑,而是追求有效。
第二,對通膨的容忍度顯著下降。疫情後的經驗,不管是德魯肯米勒或沃許對通膨都極度敏感。即便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(CPI)尚未失控,只要預期抬頭,政策就可能提前收緊。
第三,資產泡沫將被直接納入貨幣考量。科技股與房市若再度過熱,聯準會可能以貨幣工具主動降溫,終結長期以來「央行不管資產價格」的默契。
換言之,波動將不再被視為必須消除的副作用,而是可被使用的政策工具。
「降息+縮表」:短期寬鬆,長期紀律
華許目前被認為最具爭議的政策組合,是可能同時推動降息與量化緊縮(QT)。
他長期批評聯準會資產負債表過度膨脹,認為量化寬鬆(QE)扭曲價格訊號、削弱金融體系風險定價能力。他傾向於以降短期利率舒緩即期壓力,同時透過縮表(縮減資產負債表,Balance Sheet Reduction)推升長期利率,讓市場重新承擔期限風險。
這是一種「短期寬鬆、長期紀律」的結構設計。目的不是刺激資產,而是重建銀行利差與信用中介功能,讓金融體系回歸自身造血,而非永遠依賴央行擴表(擴張資產負債表,Balance Sheet Expansion)
但這條路徑極具風險。縮表將推高期限溢價,壓抑高估值資產,也可能導致準備金收縮,引發短期市場震盪。在政治高度敏感的環境下,這種波動本身就可能迫使政策退讓。
財政主導時代:央行與財政的事實性合併
隨著德魯肯米勒的兩位得意門生——貝森特(Scott Bessent)掌財政部、沃許若入主聯準會,美國正在滑向一種新的治理結構:財政主導時代的來臨。
未來流動性管理可能更多由財政部透過發債節奏與現金管理來主導,聯準會退居協調角色。2%的通膨目標可能被「軟性忽略」,以換取名目成長來稀釋債務。
這是對36兆美元國債現實的制度回應。在這種架構下,央行不再是獨立錨,而是整體債務管理機器的一部分。
真正的臨界點:政治壓力下的選擇
華許最大的考驗不是專業,而是政治。
川普需要低利率與強勢市場、投資人需要流動性,而沃許體系需要紀律。三者在經濟放緩時必然衝突。當失業上升、股市下跌、選情吃緊時,他會選擇守通膨,還是救市場?這將決定他是新的沃克(Paul Volcker,前聯準會主席),還是升級版的鮑爾。
況且,今年為美國期中選舉(midterm election),川朗普極度重視經濟和市場表現,例如川普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講話中提及美國股市52次創新高,金融市場波動會影響川普選情,華許與川普家族的長期關係可能使其更傾向於提供「聯準會看跌期權」 (Fedput),亦即市場大跌時聯準會將出手干預來救市。這與縮表的主張是背道而馳的相反方向,華許將如何抉擇?就政治,還是依專業?
央行投資化的長期代價
「華許式聯準會」最深層的風險,不在升息,而在治理邏輯的轉型。
當央行內化投資者思維,將帶來三個結構性後果:社會面向被邊緣化、波動成為政策工具,以及市場回饋主導決策節奏。這些可能導致短期效率上升及長期裂縫擴大的風險
美國正在測試一種新型央行模式,把宏觀交易哲學直接植入貨幣權力核心。它可能重建信譽,也可能放大不平等。真正的問題不是沃許有多強硬,而是當市場邏輯成為治理本身,美國是否仍記得央行存在的原初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