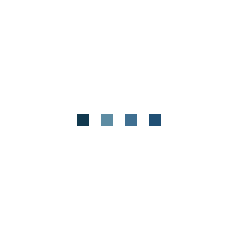核電廠的核廢料有兩種,一種叫高階核廢料,這是指核電廠中使用過的核子燃料棒,具有高輻射和高熱量,必須經過隔離上百萬年,才能使輻射量降至安全背景值。另一種叫低階核廢料,舉凡來自核電廠的衣物、工具、廢液、殘渣,以及核電廠停役後各項拆除下來的放射性污染設施等等都屬之,低階核廢的輻射性較低,但也必須被隔離靜置上百年才行。
過去半世紀以來,台灣的三座核電廠共生產了超過2萬束的高階核廢燃料棒,由於台灣的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始終沒有立法,根本無法進入選址評估階段,只能就地在核電廠內儲存。但即使如此,貯存燃料棒的廢燃料池也在2016年後陸續爆滿。加上時任新北市長,也是現任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怕高階核廢就此在新北市「定居」,因此遲遲不願發給台電乾式貯存槽的使用執照。在燃料棒無處安放下,台灣的核一、核二廠其實都是被迫提前停役。
而低階核廢的處理同樣面臨同樣的困境。2012年經濟部曾公告台東達仁與金門烏坵作為低階核廢最終處置場,因為當地居民反對,地方政府不願舉辦地方公投,選址迄今未定。低階核廢只能貯存在蘭嶼的暫時貯存場及三座核電廠內。
趕在核三廠2號機於5月17日停機,台灣正式進入非核國家之際,立法院的藍白多數於5月13日下午三讀通過《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》,修正案將核電廠運轉執照有效期再延長20年。而這顯然是一套「組合拳」,台中市政府隨後發難,指控台中電廠立刻「火力全開」,趁著夜間增加50%燃煤量,讓空汙改善前功盡棄。這樣的爭議在過去幾年來很常見,就是指控執政者為了反核的意識形態,不顧核能比較「便宜」與「乾淨」,執意燒煤,導致台灣的空污惡化電價成本失控,但這顯然是一種過於粗暴簡略的二分法:
第一、核三廠2號機將2025年5月17日停機,是在40年前開始運轉時就知道的事,要延役也不是不行,要不就如《核管法》的規定在5年前就提出申請,要不至少在1年前提出修法規劃。不過,號稱擁核的國民黨什麼事都沒做,卻選在停機前3天修《核管法》,這不是想要核電延役,這只是用來當作相罵本。
第二、台灣的核能發電佔比從1994年的30%,到2024年只佔4.7%,到核三2號機除役前僅剩3%,要補上這3%到底是要怎麼樣「火力全開」,會造成何等嚴重的空污,這其實只要簡單的數學都可以算出結果。事實上,所有的環境監測與學術研究都發現,電力業貢獻PM2.5的比率僅4%左右,遠低於移動污染源(汽機車與柴油車)的20%,遑論更大宗的境外污染源。但隨著過去10年來核電發電比率逐年下降,台灣的PM2.5從2014年的25 μg/m3逐年遞減至2024年17.5μg/m3,降幅達三成,顯見有無核電與否,與空污是否惡化沒有必然關係。
第三、擁核人士常指稱核電便宜,每度成本僅有1.76,遠低於燃氣發電的3.05。但那是以40年前所蓋的核三來計算,因為造價低,攤提成本也少,但機組老舊,運轉風險也較高,新式的核電廠恐怕就難有這種低成本。法國是歐洲的核電大國,有6成發電都來自於核電,但其電價長期以來是台灣的2倍甚至3倍以上,所謂核電便宜根本不能一概而論。
第四、恐怕也是重要的,如果國民黨這麼愛核電,為什麼前後任新北市長朱立倫與侯友宜接連阻擋核一、二廠的乾貯這麼多年,導致這麼多的高階核廢無處存放,被迫提前除役?又為何連輻射極低的低階核廢都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縣市願意收容?國民黨要發展核電,該修的法不是《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》,而是《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法》,只要核廢有解,核五能有明確的落居地,台灣才有資格討論核電的下一步。
台灣依賴進口能源,能源來源分散化是應該走的方向;在新式核能技術與安全性不斷提升下,核能或可以是一種選擇。但任何能源路徑都利弊互見,只想描繪天邊彩霞,卻選擇以鄰為豁,這是造假欺騙,絕非公民社會面對公共議題的態度。